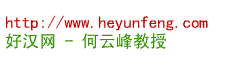表面看来,“重读马克思”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学问题。倘若这样,我们只须揭示马克思“文本”所给出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及其边界就足够了。但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重读马克思”具有远比解释学含义广泛而深刻得多的性质。它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思想之哲学性的恰当确认。
1.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结”。
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与实践的纠缠造成了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怎样看待并诠释马克思哲学的适切性问题。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究竟何去何从?是调整理论以适应实践,还是规范实践以契合理论?诚然,实际的历史选择了前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理上已经解决了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衡准问题。因为这里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因相互缠绕而形成的悖论。实际的历史可以完全不理会学理层面上的悖论,但作为哲学却不能逃避对它的追问。
当实践与理论发生矛盾时,究竟是拿实践矫正理论,还是用理论裁决实践?我们喜欢说“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表面看上去,这个矛盾好像被化解了,其实它依然存在。因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使人们迷失了判断的可靠尺度,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双重的“测不准关系”之中。是理论矫正实践,还是实践判决理论?事实上,实践的机会主义和理论的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理论的价值和使命就表征为理论对实践的范导作用。倘若理论完全是依附性的,它只是跟在实践的后面亦步亦趋地消极地适应实践的变迁,那么实践又依据什么做出调整,又何以判断实践的选择正当与否呢?反过来说,如果实践是从属性的,即完全服从理论的“命令”,那么它对理论又何以具有判决作用呢?理论的合法性来源又何在呢?显然,这里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解释学循环”。
对待此类难题,人们往往会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例如人们总是喜欢说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其实是“辩证统一”的(辩证法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讨巧的做法败坏的),如此一来它似乎就得到了解决。但这不过是一种折中主义的“遁词”而已。思想上诚实的人决不能也不应接受这类自欺欺人的把戏。问题在于,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悖论适用于哲学吗?它只是知识论所特有的难题还是人类心智领域的普遍困惑?无论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冲突,还是皮亚杰或库恩所遇到的问题,都发生在知识论的论域。问题本身固然是哲学的,但问题的适用领域却并非哲学的。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悖结”中谈论马克思的哲学,必须考虑马克思思想的非知识论性质。如果把它限制在知识论的范围内,就难以避免悖论的纠缠;如果超越知识论的视野,它就可以不去回答这个难题,而是取消这个难题。马克思的哲学固然是一种理论,但决非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这是我们今天在“重读马克思”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问题。
毫无疑问,轻视实践决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品格。马克思从未曾把自己的思想作为“书斋式”的活动来看待。同样地,当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的时候,也不应该把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当作一种纯粹“书斋式”的活动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内在地固有其指向实践的开放性。因此,思想的应用成为比思想范围内的阐释更具优先性和始源性的规定。正如伽达默尔在解释学意义上所说的:“应用本身乃是理解的一个要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应用”是人作为“此在”的在场性的介入,是“本文”通过“此在”之“在”的澄明。一旦把“理解”或“解释”定位于本体论层面,实践性及其优点就充分凸显出来了。这种广义的“理解”或“解释 ”,首先就包含着思想的实践力量和它所显示的意义的生成。从这个角度说,“重读马克思”不可能在思想的范围内实现,它只有通过实践及其反思才能完成。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对实践应用的反思,是由于我们以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缺乏反思的态度,这不仅削弱了实践对哲学的建构意义,而且有可能丧失对实践经验的鉴别能力,以至于造成为了满足实践的策略需要而牺牲理论原则的后果。马克思当年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此在性的介入,为他的现象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作为马克思的诠释者,也只有从“此在”入手,才能与马克思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才能发出自己的追问并寻求可能的回答。否则的话,无论我们怎样阅读并诠释马克思的“文本”,也不可能成就一种有生命的意义之生成。
2.马克思思想的“面相”及其定位。
马克思及其思想是一个“多面体”,这也恰恰是一位先知式的思想家所必然具备的特征。其丰富而深邃的内涵,总是表征为不同的思想“面相”,有时甚至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马克思是革命家、反抗者,是现代性的批判者,是思想家、学者,如此等等。从马克思的著作所表达出来的口吻看,作者无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愤世嫉俗的人。他在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往往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马克思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诊疗者”。这种印象是真实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因为若仅仅把马克思的形象“锁定”于此,就将不能不遮蔽马克思所曾达到过的最高境界,从而低估了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意义。关键在于,作为解读者的我们必须确认其最本质的维度。这应该成为“重读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对马克思的角色定位和思想“面相”的识别,将直接关涉到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角度,甚至决定着我们的评价立场。
诚然,马克思思想的不同“面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期待视野。人们往往选择那种最契合自己偏好的“形象”加以叙述、描绘和发挥。时代维度是一个无法被超越的变量,构成重读马克思的期待视野的历史前提。问题在于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是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契机,又是过度解释马克思的诱发因子。任何一种可能的解释都是一种意义的生成和重建,而不是意义的绝对再现和还原。解释学似乎赋予了我们一种“六经注我”式的特权,但它同时又可能成为误读(无论是无意还是故意)的借口。现代解释学或多或少地怂恿了解释者的这种主观随意性,使“六经注我”存在着沦为“过度解释”的危险。但无论如何,来自“文本”的牵制和约束是无法被“读者”缩减掉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是有其自身生命的。因此,在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马克思思想的“面相”加以辨识,同时保有能够达成主体间性意义上之共识的信念。
从知识分类学的角度说,马克思思想无疑涉及众多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些学问,马克思并没有采取职业学者所特有的专门家的姿态。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其优点。因为他的哲学家角色决定了这一切学科不过是为他的反思提供前提和对象而已。另外,它们也只是构成其现象学揭示的表征手段。专门家总是拒绝和排斥其他学科视野的,因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盲性”关系决定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切学科必须得以贯通,才能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哲学建构的意义。唯其如此,它们才能构成辩证法这一人类存在结构的现象学展现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和环节。意大利社会学家菲尔弗雷多·帕累托说:“马克思的话像蝙蝠。人们在其中既能看到鸟,也能看到老鼠”。之所以如此,乃是由马克思思想的多义性决定的。但马克思思想的内核和总体性质是哲学的而非其他学科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所采取的形上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所特有的批判姿态。就此而言,马克思不仅是一种人格化了的批判精神,而且是批判尺度的化身。如果说苏格拉底是古代社会的“马虻”,那么马克思则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社会的“马虻”。
拘泥于知识论建构者的形象,就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的知识论期待,恰恰是造成对其失去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马克思思想不能发挥知识功能时,我们就误认为它缺乏回应时代、回应实践、回应现实的冲动和能力,进而怀疑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就像因“哲学烤不出面包”就抱怨哲学一样。期望马克思为未来开出所有的“药方”,且对经验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预期,这无异于把马克思当成上帝。因此,决不能认为只有马克思能够解释一切,其思想才是值得肯定的。这样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知识了。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思想决不是一种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哲学批判的衡准和反思的尺度。这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真相”。如此定位,也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思想之所以遇到时代的“挑战”和“难题”,乃是由于我们对马克思形象的误解和不恰当定位造成的。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需要我们在马克思思想的不同“面相”之间作出选择:是作为知识建构者的马克思,还是作为终极尺度之人格化的马克思,抑或是作为智慧之源的马克思?
3.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
在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所谓“深度解读”,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层次:一是把马克思没有说出的说出,它不能仅仅满足于字面含义的考据、辨析和释读,而是通过这些必要的前提,进而揭示马克思思想的隐秩序和潜结构,所谓“得意忘言”,以凸显其“微言大义 ”,揭示词句背后的意蕴;二是把马克思没有说完的说完,所谓“接着讲”,这应该是一种合乎马克思思想内在理路的引申和发挥;三是与其他哲学之间的比较和会通,使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在思想上能够相互发明、相互解释;四是习得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注重的不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也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追问方式。这里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关系。
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并捕捉到马克思哲学的真正问题和它的实质之所在。一旦自觉地寻求这种深度解读,就将开辟出过去的诠释未曾涉及到的新的意义域、新的思维空间、新的诠释的可能性,从而有可能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新境界。
按照深度解读的要求,我们将会发现,如果说康德提出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那么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则是“超验规定的历史建构如何可能?”马克思问题的实质在于追问超验与经验之统一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未曾如此明确地表述过自己的问题,但他的全部思想向我们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真正困难不在于超验与经验的划界,而在于它们的统一。传统哲学只要有资格成其为哲学,就不能不正视这种划界,然而在超验与经验的统一问题上却未必都能够有一个恰当的处理。因此,这也成为判断一种哲学是否彻底、是否真正实现了自我完成的重要标志。同康德的问题相比,马克思的问题其困难程度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完备性而言,马克思的问题优越于康德的问题。因为康德的追问方式仅仅局限于知识论的范围,而且最终并没有克服二元论的缺陷。马克思则超越了知识论的限囿,摆脱了二元论的陷阱。首先,马克思不再把超验性规定狭隘地理解为一个知识论范围内的问题,而是把它置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层面,从而使其进入了人的历史语境之中。其次,马克思找到了人的存在这一生成超验与经验之分野的发生学前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超验规定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同时也就意味着超验与经验作为两种视野之对立的扬弃,它是通过人的“积极的存在”亦即所谓实践得以实现的。这一过程表征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呈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实践既是一种哲学视野,也是本体论的内在前提,还是一切矛盾得以最后消解的历史基础。
“过犹不及”。我们之所以追求深度解读,就是为了克服解释不充分的缺陷(所谓“不及”)。然而,在对马克思“文本”进行深度解读时,又要避免解释过度(所谓“甚解”)。恩格斯在谈到“老年”黑格尔派时曾经指出:“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得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时刻警惕“懂得一点‘无’,却能写‘一切’”式的误区。